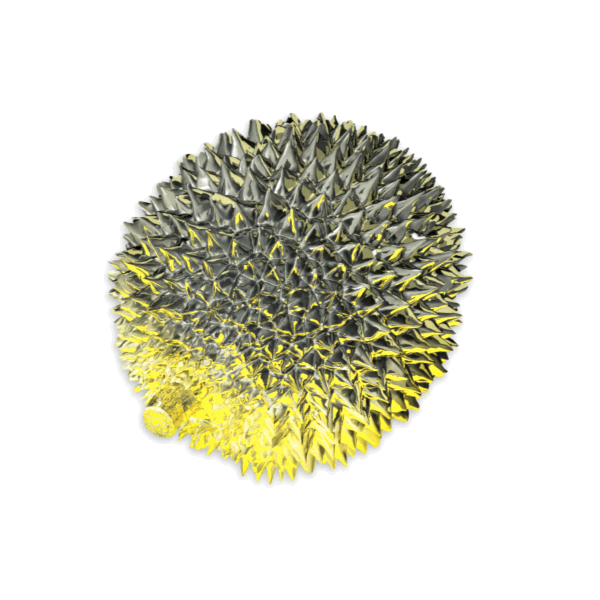罗德尔·塔帕雅在工作室创作。由艺术家惠允。
菲律宾艺术家罗德尔·塔帕雅(Rodel Tapaya)于2007年打造的新传统系列画作《民间叙事》(Folk Narrative)承载着艺术家探索和研究当地传统民间故事并经由艺术转化赋其新生的希冀。艺术家以特定寓言、神话人物、信仰或历史事件为原点,将混种动物、植物和物件的有机群体、相互关联的生物和一片片抽象形态建构成杂乱丛林,进而展陈为一个复杂而稠密的意义网络。他的大幅具象构图映射出菲律宾在殖民历史和文化共融的标记下所凸显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身份认同。身为时代的写照,这些画作也烘托出切入社会时事的讽喻,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并揭示了当代政治、社会和生态问题。
怀揣对菲律宾历史和传统民间故事的热情,罗德尔·塔帕雅不断收集当地口述叙事,并研究它们与菲律宾成为西班牙殖民地之前的种种关联。他还将调查触角伸向西班牙、美国和日本文化对菲律宾传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当代社会的表达。纵然民俗内容丰富多样,但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忽视。通过收集寓言、传说和民间信仰,并通过批判性的艺术实践让其重焕新生,艺术家希望在传递文化遗产之余,亦可质疑国家当前的权力体系。
创作语境与艺术驱动力
焕新当地民间故事

罗德尔·塔帕雅,《应许之地》(三联画),2016。第一幅。布面丙烯,243.8 x 335.3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罗德尔·塔帕雅于1980年在菲律宾黎刹省(Rizal Province)蒙塔尔班市(Montalban)出生,家里人多,家境一般。父母以熏鱼为生,所以他八岁时就负责购买包裹熏鱼的旧报纸和杂志。交给母亲之前,他会先看看生活风尚版,把图片和艺术复制品剪下来收藏。通过这种艺术初体验,他认识了安妮塔·马赛赛·何(Anita Magsaysay-Ho)、毛罗·马朗(Mauro Malang)和本尼迪克托·卡布雷拉(Ben Cabrera)等艺术家。他的艺术实践多半也源自这种与艺术结缘的情境,时至今日仍以时代错置和多重元素的拼贴和集合为主。之后,他很快拿起画笔,赴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课程,开启了自己的艺术征程。
塔帕雅的创作源动力来自家乡丰富的民间传说,那是个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 Mountains)的山坡上以峡谷和传说闻名的小镇:据说民族英雄贝纳多·卡皮奥(Barnardo Carpio)正是被困在两座彼此相望的山岳之间。传说有不同的版本,结合了西班牙殖民前的民族元素与西班牙文字和他加禄(Tagalog)民间诗歌。这个传说在19世纪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后,不断地被人们重新诠释。无论是巨人英雄在与恶棍交战时被囚禁,还是他试图阻止两座山岳的争吵时被困住,都与菲律宾希望摆脱殖民身份的民族呼声划上联系。独立运动期间,一些民族独立者来到山中乞求英雄的祝福。这种民间传说的力量激发了塔帕雅的想象力,他也会忆起自己孩提时对传说的研究。面对这些当年只能口口相传的故事,艺术家试图通过形式与色彩让它们重获生机。

罗德尔·塔帕雅,《四个世纪之后的假贝纳多·卡皮奥》,2006。粗麻布面丙烯,121.92 x 91.44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艺术家以自己在家乡一带收集的当地陈年往事、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为灵感,于2007年开始创作《民间叙事》系列。一开始,塔帕雅只是想把先故事变成图像,然后再探索它们多元的解读方式以及故事与现实的关系。再往后,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结合两个步骤,不仅解构和重构它们的多元内涵和象征力量,而且将自己的收集范围扩大到菲律宾其他地区。“我喜欢民间故事、神话和传说的超现实性和高于生活的特质”。艺术家仍在不断尝试以绘画形式反映内容的不同方法,系列创作还在进行之中。他也通过此举来挖掘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之前的民族根源,并思考从西班牙到日本的历代殖民者如何影响当地文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当今社会的某些风貌。
被誉为“菲律宾民俗之母”的达米安娜·尤金尼奥(Damiana Eugenio)指出,部分传统民间故事直到19世纪后段才开始被收集。不过,大部分最初收集的故事都已不复存在,这就让全面性研究迫在眉睫。塔帕雅将艺术创作植根于菲律宾的民族历史和民间故事中,以期再度激活它们的生气,凸显复杂而浓厚的民族文化。“说到认识和热爱国家,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教授历史。我也发现,作为一个民族,菲律宾需要努力做到这点。通过创造和讲述历史,展示本族文化的美好和错综,我相信艺术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期待国家灵魂能够再获生机。”
生动丰富的民俗:各方影响的共融与渗透

罗德尔·塔帕雅,《猴美人》,2013。布面丙烯,198 x 136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受西班牙王室之托探寻“香料群岛”,首次到达菲律宾。他一到达现在被称为宿务(Cebu)的地方,就组织了大概800名原住民接受洗礼,还将一个刻有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木雕送给了岛上的女王。天主教很快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宗教。
成为西班牙殖民地之前,菲律宾原住民信奉至尊神巴塔拉(Lord Bathala),这个伟大的造物主还派了几位侍从为人类调解纷争。当地人还敬重其他的神明,经常举行赞美神灵的宗教仪式。他们的信仰体系并无经文,靠着口述方式将神话、谚语、习俗和行为准则代代相传。不过,他们倒是很轻易地就接受了天主教,并将天主教的圣人同化到当地神灵的序列中。此举的结果就是,地方神话和传说吸纳了部分西方宗教元素,产生颇为独到的宗教共融。天使与当地神灵联系起来,基督教的宗教符号被再次挪用,宇宙观得以进一步充盈。基督教人物还与超自然古生物共存,比如据称仍在菲律宾出没的当地恐怖吸血鬼阿斯旺(Aswang)、以内脏为食的妖怪、狗人、女巫和食尸鬼。
19世纪末,旨在摆脱西班牙殖民者、实现民族独立的地方民族运动兴起,使这些神话元素和传说得以复兴。何塞·黎刹(Jose Rizal)在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也是菲律宾具有先驱意义的民俗学家和神话学家。尤其是他对传说人物贝纳多·卡皮奥(Bernardo Carpio)的解读,突出了后者作为民族解放者的身份。彼时著名的反叛者变成了此时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生平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汇入了当地民间传说。艺术家感兴趣的恰是将历史事实与神话传说隔开的模糊边界。
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宣布对菲律宾施行军事统治,随即引发了美菲战争(即菲律宾独立战争),直到1902年美国在菲律宾建立文官政府才结束。菲律宾在二战期间一度被日本占领,直到1946年终获独立。虽然“美国势力催生了免费的全民公办教育体系、法治和法院制度”,但也带来了至今仍深植于当地文化中的快餐文化和美式生活元素。有些菲律宾人在追忆过往时将国家历史描述为“修道院里300年,好莱坞里半世纪”,不过塔帕雅觉得这种归纳太过简单。接踵而来、层层交叠的殖民势力塑造并转变了如今的民族认同和传统的集体叙事,而艺术家旨在用自己的画作来剖开这些力量底层的复杂属性。
艺术家认为民间故事能让我们更好地领会历史,而且反过来说,历史也为民间传说的构建提供指引,所以他很看重这份知识的传播。菲律宾拥有七千余岛屿,87种地方语言,文化极为多元,所以这份工作难度不小。不过塔帕雅却欣然接受这种多样性,因为他并不想展现菲律宾民族认同中的任何共同之处。
腐败、庇护与专制力量

罗德尔·塔帕雅,《奴隶贩子》,2015。布面丙烯,243.84 x 335.25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在塔帕雅看来,西班牙殖民者保持了基于大庄园(Haciendas,即拥有土地的不动产,起初为种植园)的封建制度,这依旧是菲律宾人当下心态的根源,往往觉得自己是依赖政府的幼儿,而不去寻求自己的解放。此外,这种无法脱离腐败的庇护制度导致不平等加重、贫困加剧和经济落后。“虽然菲律宾享有两党民主制度,但政治庇护保住了本应被撤换的腐败或无能官员,而主要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国会也经常阻挠重要土地改革立法的及时通过。在20世纪60年代末,尽管许多邻国正在迅速工业化,菲律宾却因为精英阶层所青睐的进口替代政策而放慢了经济增长的脚步。”刚刚独立之际以及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一度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可到了2016年,九成菲律宾人被归为下层或工人阶级,其中27.9%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哪怕过去几年经济有所增长,但贫困状况仍然很严重。(......)约33%的五岁以下儿童都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
民族独立后的若干年间,菲律宾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近几十年来,军队势力支持独裁政府,将天平向精英、官僚和商人倾斜。从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颁布军事管制法到他的政敌小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S. Aquino Jr)被暗杀,再到2016年无视人权法律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 in 2016)当选总统,塔帕雅用狂欢式的画作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混乱的数十载。在当今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他觉得恐惧无处不在。自杜特尔特当选以来,官方引爆的禁毒战争显著拉高了被法外处决的人数。仅在他执政首年,据信就有多达一万两千人被杀,而行凶者无一受到审判。与此同时,他的一众亲信给非法伐木开绿灯,批准采矿特许权,导致该国森林被大幅滥伐,生态环境和当地社区深受其害。大自然是贯穿塔帕雅作品的常见元素,虽然因人类所为而遭污染和破坏,但郁郁葱葱的丛林似乎总能占据主位:在艺术家心中,大自然比人类活动和衰败更为经久。
艺术家的研究维度
收集各类民间故事

艺术家的藏书。由艺术家惠允。
“我尽力寻求不同的灵感来源。我喜欢了解菲律宾文化、故事、历史......我试图探索不同流派,发现它们与个人作品或主题的关联。”
塔帕雅认为自己主要从事研究型艺术实践,因为他多年来不断收集和调查被西班牙殖民前的民间故事和地方叙事。他不仅四处搜寻传说,还收集古谚、谜语、游戏和戏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资料库。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文字材料,不过也会向老人家打听口头叙事,特别是来自家乡所在地北吕宋岛(Northern Luzon)和父母的祖籍地米沙鄢(Visayas,位于菲律宾中部)。他总是以随意的方式开展实地调研,也没有系统性或学术性地收集故事。一般就是在途中与当地人交谈,让他们谈谈童年回忆。
塔帕雅的调查范围非常广泛。民族学家达米安娜·尤金尼奥(1921-2014)的作品是他的主要参考资料,这位菲律宾作家和教授将毕生精力用来研究和编纂菲律宾民间传说。她把民间故事分为若干类:动物故事或寓言、魔法故事、幽默故事、宗教故事、小说式和教诲类故事。虽然她在这个主题上著作等身,但她还是强调了更加全面系统地收集菲律宾各地口头叙事的迫切性。她也觉得这些故事没被很好地诠释,并采用一些国外故事进行比较性分析,例如灰姑娘与王子的会面之处由舞会变成了教堂,把这个西方童话故事进行了菲律宾本地化加工。另一种民间故事分类法来自梅莉·莉安迪乔·洛佩兹(Mellie Leandicho Lopez)撰写的菲律宾民俗理论著作——《菲律宾民俗手册》(A Handbook of Philippine Folklore)。另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是弗朗西斯科·德米特里奥(Francisco Demetrio)的《菲律宾民间信仰和习俗词典》(Dictionary of Philippine Folk Beliefs and Customs),作者在菲律宾南部卡加延德奥罗(Cagayan de Oro)的泽维尔大学博物馆(Xavier University Museum)担任菲律宾民俗与民间传说中心(Philippine Folklife and Folklore Center)主任,艺术家也去那儿考察过。词典按主题编排章节,比如动物、阿斯旺或女巫、死亡、功绩和庆典等。德米特里奥还写过《菲律宾的神话与象征》(Myths and Symbols in Philippines)一书,描述并研究了早期菲律宾神话的发展,同时将宗教、神话和口述传统联系起来——正是塔帕雅研究的核心要素。
除了介绍民间故事的书籍,还有提供线索的电视节目。脍炙人口的睡前故事节目《巴斯扬奶奶》(Lola Basyang)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陪伴艺术家度过了童年时光。巴斯扬实际上是菲律宾作家塞维里诺·雷耶斯(Severino Reyes)的笔名,他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传统短篇儿童文学作品,登载于杂志和漫画书上。看过这个节目后,塔帕雅不由地向身边人打听起当地传说。他把一位老妇画在作品《奶奶的故事》(Grandmother's Tale,2021)中,用奄奄一息的祖母形象暗示着讲故事——一种传播故事的艺术形式——濒临绝迹。
人类学与历史
何塞·黎刹和其他一些民族英雄也积极推动了地方民间故事的传播,特别是前者在1891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民族英雄的生平和传说是也属于塔帕雅试图追溯的集体记忆。例如,他曾调查了另一位独立时期的民族英雄马卡里奥·萨凯(Macario Sacay),美国人于1907年将他绞刑处死,还通过宣传来诋毁他的形象,结果人们只记得他是个强盗。
研究地方谜语、谚语和游戏同样需要人类学的方法。有些民间故事通过表演形式呈现,把叙事与戏剧艺术相结合。在菲律宾长期生活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亨利·斯科特(William Henry Scott)写过《描笼涯》(Barangay)一书,通过深入研究16世纪的菲律宾来描述西班牙殖民者刚刚踏上这片土地时的感受,以人类学视角为那个年代提供了丰富注解。而在更接近当代语境的作品中,他主要受菲律宾人类学家费利佩·兰达·约卡诺(Felipe Landa Jocano,1930-2013)的启发,后者是以参与观察法开展菲律宾民族志研究的先驱。约卡诺因实地调研而闻名,特别是著作《作为生活方式的贫民窟》(Slum as a Way of Life),让艺术家汲取灵感并创作了最新的《剪贴绘画》(Scrap Paintings)系列。在描绘城市贫困社区的生活时,除了参照自己在贫民窟度过的童年时光,塔帕雅大概率也借鉴了这位人类学家的人文主义手法。约卡诺还记录了一些地方民间故事和史诗,不过有些书比较小众,艺术家只能从二手资料中找到它们的踪迹。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和以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对艺术家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影响。艺术评论家大卫·艾略特(David Elliott)指出,艺术家必须“学会把一整本书浓缩在一组互相联系的图像内,只用一幅画面就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些阅读经历和研究实践非但没有限制他的视野,反而使“图像在他的想象中喷薄而出”。
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
叙事者

罗德尔·塔帕雅,《巧克力废墟》,2013。布面丙烯,304.8 x 731.52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Tapaya defines himself as a storyteller and his paintings tell stories of their own, an interwoven combination of the artist’s research material with his own imaginative power.
塔帕雅把自己视作叙事者,画作交织了研究资料和自己的想象力,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他偏爱使用大幅画作,让观众感受作品的局部,部分叙事系列的作品甚至长达七米多。大尺寸意味着他能够专注于大量的微小细节,充分发挥构图上微观和宏观视角之间的对比效果。为了在读书时赚点钱,他曾经为室内设计师画过房屋结构图,学到了不少错视画和大型壁画创作的经验。超大幅作品是壁画家的悠久传统,对他的影响不小,比如以历史构图而著称的菲律宾艺术家胡安·卢纳(Juan Luna)和卡洛斯·莫德斯托·“博通”·维拉卢兹·弗朗西斯科(Carlos Modesto “Botong” Villaluz Francisco),还有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科(Jose Clemente Orozco)。在他们的作品中,蕴藏在社会现实主义中的强烈叙事维度对向来偏爱具象画的塔帕雅来说尤为重要。
塔帕雅将大量的寓言和故事揉捏在自己的作品中。他的构图如同丛林一般,密密匝匝地缠结着不同人物、神话生物和自然元素,而且从不留白。艺术家用这份稠密和复杂来映射菲律宾因传统、方言、民族和文化交叠而生的多样性。同时,让人眼花缭乱的细节不断堆积,也呼应着菲律宾人对恐惧留白(horror vacuii)的敏锐感受。因为他用拼贴画和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为创作素材,所以大部分作品都呈现出明亮色调。艺术家也乐于在令人欢快的审美基调和黑暗阴郁的作品主题上形成反差。

罗德尔·塔帕雅,《多瓣之美》,2012。布面丙烯,244 x 426.72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民间故事常以动物来代表人类特定的品质或象征。通过反复出现的动物和主题,塔帕雅依靠奇妙的动物寓言来支撑自己的叙事和讽喻。担任骗子一角的动物通常是猴子,不过猿猴也被拿来模仿人类及其欲望。在作品《多瓣之美》(Multi-Petalled Beauty,2012)中,一只歇息在怪诞植物上的猴子化形为人,只为追求美貌和青春永驻。一张没什么生机的苍******庞从香蕉一般被剥开的皮肤中现出,旁边有群羊看着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只有一头羊慵懒无力地盯着我们。这些羊就是克隆羊多莉和当代克隆研究的化身。作品下方是一条鳄鱼,意指那些图谋不轨、妄图利用新技术制造假药来欺骗世人的恶人。出现在其他作品中的猪、鳄鱼和青蛙体现了贪婪和权力,而头骨图案则代表来世、地府和死亡。同样,在菲律宾神话中,神鸟Manaul用喙啄开了一根竹子,从而诞生了人间第一对男女,而它也以不同形态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例如在《巧克力废墟》(The Chocolate Ruins,2018)中制作巧克力。
塔帕雅还会利用建筑细节和参照物将叙事拉回到特定语境中。作品《Whisper Cutler》(2014)以一座带古典风格主立面的混合式建筑为背景,一只打着领结、令人恐惧的野猪似乎在传播恐慌。在艺术家看来,白色建筑烘托出权力的意味,暗示着充斥西方影响的政府所在地。他在《Nang Wala Pang》(2010)中画了一个老房子,这种田间茅屋(nipa house)是菲律宾北部某部落的典型建筑,艺术家就用源于此地的房子给故事找到了归宿。

罗德尔·塔帕雅,《Whisper Cutler》,2014。布面丙烯,193.04 x 152.4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哪怕作品有着准确的参照物,塔帕雅却不想只吸引菲律宾国内的观众。除了一些民族特有的内容,许多神话和故事都极为相似,哪怕它们的起源不同,而清晰无误的艺术图案也具有普适性。他愿意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Farm)作为隐喻的另一来源。他也认为,古往今来,打人类诞生起,人类对待环境和世界的做法总有相似之处。
有机过程与拼贴
绘画的起点可以是一个故事,一则新闻,或是一个简单的形状。塔帕雅从一个给定的元素出发,把研究材料与想象力对接,让视觉图像蓬勃生长。完工之前,他总会停顿数次,所以绘画过程非常缓慢。同时处理多个构图的做法为作品赋予活力,使想象力有充足的时间去拓展。
从2011年起,艺术家就惯于以拼贴来开启创作过程。在那以前,他只是根据记忆和想象来先打个底稿,然后完成作品,用一张大画布来承载所有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做法让他觉得束手束脚,所以他随后决定加入拼贴元素,在丰富图案和色调之余,还能为构图带来意外之喜。此举也为单调的平面图案和更为具象或现实的元素之间提供了充分的对比,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神话与现实间的混淆或滑脱。“这种做法就像创造杂合式的现实主义,我觉得它和神话的本质和创造相似,以及在当下让这些老故事讲出新意思。有时候,神话更接近事实,而事实看上去更像是虚构的”。

罗德尔·塔帕雅,《魔蛙》,2014。布面丙烯,233.68 x 355.28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画作先用拼贴元素初步打底,乍一看背景混乱不堪。塔帕雅把拼贴部分扫描,然后打印出副本,就可以在上面作画,添加多层形状和意义。“这是个有机的过程。我通过图像和形态寻求下一步的灵感,再用思维导图记录想法,核心想法不断发散,产生更多的点子。和植物生长一样,想法从小到大,发芽生长。”通过长期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艺术家在混乱的集合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路径,将图像、色彩和形状逐步串接起来,并将所有元素依次排序。许多画作都近乎“逼真地”表达出这种有机流动和多级转变——无论性质如何,不同形态都像植物般生长和延展:伸长的手臂,过度弯曲的脖子,从动物头顶长出的尖刺,从物件中长出的根茎,各色生物发出的枝丫,再加上抽象的形态,所有一切,相互交融。
正是这样的手法,使得源自不同时空范畴、各式各样的大量人物和图案共存于塔帕雅的作品中。集合或拼贴的创作原则将一直以来两两相对的事物统一起来:神话生物与真实人物并置,往昔幽灵与时事和动物混搭、人与物突然并排而现。在层层叠加的作品中,有些图案真像是从背景中飞翔而出,或是不知从何处就冒了出来。独创的构图散发出荒诞的意味,与此同时,全新的意义和叙述也随之而来。

罗德尔·塔帕雅,《片刻喜悦》,2018。布面丙烯,243.84 x 335.28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在《片刻喜悦》(Instant Gratification,2018)这件作品中,一只身穿白色西装的巨猴出现在奇幻丛林中,超长的左臂拿着一串背在小乌龟背上的香蕉,脚下有一群幽灵般的人在小房子前排着队,可能是急着买彩票。房子旁边画了一台老虎机,和房子几乎一般大。从这部分开始,不同的抽象形状就沿着一个三角形图案向上和向下生长。这些元素轮廓齐整,给人一种奇怪的另类感,但颜色又与背景非常和谐:所以说,它们既与景观格格不入,又从属于景观。在画面左边,塔帕雅利用逐层树叶来营造景深,尽管他没有采用常规的透视原则。因此,难以言状的色块和形状在彼此上方并置,让画中万物皆显生硬和滑稽。画中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已然赋予作品非理性维度,而这种静态组合模式进一步增强了这属性:树干长着眼睛,猴子的头颅在膨胀,透明的钻石飘来飘去,而忙碌的猴子在另一只小乌龟的密切注视下捡着与体形不相称的灌木。
这幅画以何塞·黎刹讲述的菲律宾传统故事《龟与猴》(Ang Pagong at ang Matsing/ The Turtle and the Monkey)为灵感。在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猴子捉弄了乌龟,但后者最终报了仇。具体来说,摆在桌上的石臼和研杵代表猴子希望惩罚乌龟的方式。塔帕雅在这里把故事放到了当代语境中,借此表达同胞们的贪婪和利己主义。裹着黑色长袍的小幽灵也许指向大部分民众,为了求财或求物而四处游走。他们也是艺术家在不同作品中的常设人物。

罗德尔·塔帕雅,《羔羊祭品》,2015。布面丙烯,244 x 335.28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通过拼贴,艺术家得以在这些具有具象的象征元素上做点文章,也恰当地表达了菲律宾民族认同的共融性,比如说不断地将天主教肖像或符号与他加禄文化元素相结合,从而反映了塑造菲律宾现状的复杂历史层次。《羔羊祭品》(The Sacrificial Lamb,2015)说的是两兄弟牺牲了心爱的妹妹,盼望此举能换来花园里长出点儿能吃的东西。艺术家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病态思维,但又有力地描绘了爱意之举。故事把宣扬耶稣为人类而奉献生命的天主教与菲律宾传统信仰联系在一起。画作里,一片血雨中,两兄弟在自家老式小屋旁的花园里劳作,当地人把这种菲律宾特有的耕作技术称为kaingin,也就是通过砍伐和焚烧林木来开垦土地。在他们身后那座黑暗的远山上,艺术家用三个十字架代表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骷髅山(Golgotha Hill)。同样,艺术家反复使用的人类头骨和羔羊图案中也普遍存在天主教的影子。《应许之地:月日星》(The promised land: the moon, the sun, the stars,2016)等作品与《圣经》也有着直接的关联。塔帕雅还巧妙利用画作格式,充分体现集聚多重信仰形式的菲律宾文化的原创性。例如,《猴美人》(Monkey Beauty,2013)用了一块水滴形的画布,象征着为佩戴者带来好运的传统护身符。在画框的设计上,艺术家找到了通常为教堂设计祭坛饰品的当地工匠,材料选用黄铜板和锡板。因此,仅凭格式设计,这幅画就模糊了不同信仰和信念之间的区别。
当代讽喻和形变

罗德尔·塔帕雅,《阿斯旺进城》,2018。布面丙烯,243.84 x 426.72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拼贴过程中,互不相干的图案构成混乱而荒谬的整体构图,而所有事物之间强烈的互相关联又抵消了这一乱局:时间、地点、历史事件和神话共处一框,在接二连三的形变中孕育彼此。艺术家精心挑选的透视效果超越了简单的共融,强调了历史与现状的相互作用:历史指明现状,现状诠释历史。
这种转变过程在《阿斯旺进城》(Aswang Enters the City,2018)中尤为突出。这幅画描述了菲律宾民间传说中的混合物种阿斯旺入侵城镇的过程。这种怪兽有点像猪,舌头长得夸张,算是一种吸血鬼或“以内脏为食的妖怪”,所到之处,大肆吞噬,引发恐惧和混乱。到了早上,它们就会变成普通人的模样。画作左边,形变正在进行中,警察的面庞中冒出猪头的轮廓。同时,体型庞大的阿斯旺正在斩落动物的头颅,撕开它们的肉身,无视用脚勾着大蒜来消灭它们的无头或长着人脸的白鸟。老百姓一般都觉得大蒜可以对付这些超自然物种。来自远古信仰的血腥场面象征着当代菲律宾的人间惨剧——多在夜间发生、让人们恐慌不已的法外处决事件,其实就是暗指杜特尔特总统在2016年竞选时的那番话:“请随时联系我们,联系警察,或者有枪的话就自己动手——我支持你们。射杀[毒贩],我会给你颁发奖章。”在这场令人惊恐的角色转换中,警察正在变成罪犯,而普通公民也能合法地宣称自己就是警察。
在作品下方,一个蒙面人手指某处,仿佛确定了目标。头罩是枯叶编成的筐子,这是武装团体菲律宾爱国者联盟(Makapili)的典型装扮。“Makapili”这个词的原意是“选择”,因为联盟成员一般会指定自己要杀的对象。该联盟成立于1944年日占期间,目的是辅佐日军,监视当地居民。虽然这帮菲奸算不上什么爱国人士,但他们把自己称为“菲律宾爱国者联盟”。战争结束后,联盟并未解散,继续以恐怖手段为非作歹。这个蒙面人是另一幅作品《蒙面证人》(Hooded Witness,2019)的中心人物。他手拿望远镜,头罩遮住了脸部特征,只能看到双眼。作品上部画了一名身穿制服的怪物警察,长着一个凶神恶煞的狗头,手里拿着几只死老鼠。他的皮肤是绿色的,右臂末端不是手,而是长出两条鼓着大眼睛、节节疤疤的绿蛇。对塔帕雅来说,这些人“就像猎杀老鼠的狗。他们把旁人视为低人一等的害虫,肆意杀害之余还波及无辜,让所谓的战场上只剩下寡妇和孤儿”。

罗德尔·塔帕雅,《蒙面证人》,2019。布面丙烯,152.4 x 121.92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此处的现时接续着过往,徐徐展开。这种相互依存在所有涉及殖民时期的画作中也很明显,比如艺术家在《巧克力废墟》(2018)中指出,沿袭自殖民国家的封建制度仍在塑造着当今的菲律宾社会。在这件大幅画作中,造物神鸟将可可豆倒入加工机器,然而加工产物却消失在一个由物品和荒谬物种组成的茂密丛林里。神鸟背后有一朵巨大的黄色可可花,生出一条长蛇,蛇身在混乱景观中无影无踪。除了具象呈现殖民年代的典型产物,此处的可可也代表腐败与西班牙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失衡权力体系。
最后,形变的有机过程和人类、生物和物品之间的整体互联反映了艺术家对生态问题的关切。例如,在《麦纳麦的住所》(Manama’s Abode,2013)中,岩石中直接长出了一个男人的身体,他的一只手臂长出一只鸟,而第三只石手还嵌在山石中。麦纳麦是菲律宾南部马诺博(Manobo)部落信奉的神灵。作品通过在构图中心位置绽放的宏伟巨花来突出大自然的力量。塔帕雅引用的神话和寓言讲述了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其力量远胜人类的行为。不过在更为细致的局部或背景中,观众可以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的迹象,无视联结所有生物的相互依存性。以《巧克力废墟》(2018)为例,作品的场景选在菲律宾保和省(Bohol province)的巧克力山,那里曾于2013年遭遇致命的地震。作品中,面对地震引发的山崩,穷人四处寻找遮蔽之所,而巨鸟还在为了赚钱不停地制作巧克力。
结语

罗德尔·塔帕雅,《麦纳麦的住所》,2013。布面丙烯,193 x 152.5公分。由艺术家惠允。
透过《民间叙事》系列,罗德尔·塔帕雅结合古老的菲律宾口述民间故事,将其转化为艺术形式,并赋予其当代力量。他利用研究和调查来收集门类广泛的寓言和故事,让它们重焕新生。虽然艺术作品有密集的层次和复杂的 表意,但大幅格式、明亮色彩和震撼图案贴切地支撑了他的叙事。
研究型艺术实践不仅帮助菲律宾人牢记自身的传统,还能助力外国人发现这些传统。然而,传统的焕新和传播并不总能清晰传达信息。经过连续的形态变化,故事原形被分割、重释和重组,也许就会消失在艺术家叠加其上的叙述之中。塔帕雅使用叙事语言和现成的媒材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并对当今菲律宾的社会现实加以评论。如此这般,他保留了根据当代语境而重构和再释民间故事的传统,与何塞·黎刹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利用寓言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转换过程中难免会丢失原先的部分内容。此外,艺术家通过视觉呈现口述传统,也许会侵蚀民间故事自古以来的重要特点——口述文化。
如上所述,塔帕雅展示了民间故事象征性和叙述性语汇的力量,它们依旧能反映当代时事。在他的画笔下,人物以超乎想象、超越各种文化框架的表现力展开。也许他接下来要尝试摆脱拼贴和现存的视觉参照,发明一种新的叙事语言和形式语法,用焕然一新的创作形式来转译活力十足、内容丰富的菲律宾口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