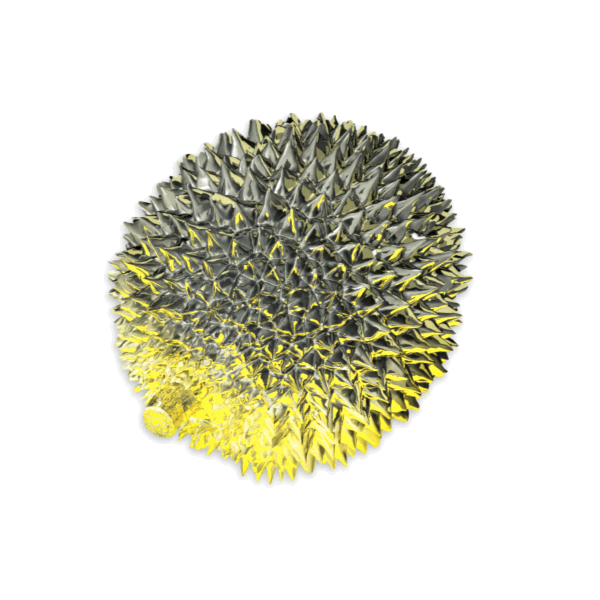沙迦双年展现场,2019。
所有图片均由艺术家惠允。
越南艺术家阮俊(Tuan Andrew Nguyen)为第14届沙迦双年展(Sharjah Biennial 14)创作了四联屏视频装置《成为祖先的幽灵》(The Specter of Ancestors Becoming,2019),他将目光投向了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越南社区,尤其是印度支那战争中代表法国殖民势力参战的塞内加尔士兵的后代。作品源自艺术家在达喀尔的实地研究,在艺术家与越南裔塞内加尔人社区的合作中形成,突显了萦绕不去且影响至今的殖民主义幽灵。影片中的虚构叙事源于业已成年的越南裔后代对历史和童年的想象。电影的拍摄语言遵循人的记忆习惯,通过重复、档案影像和虚构对话的方式展开非线性叙事。最终,视频探讨了“身份认同”和“混血(métissage)”这两个话题,以及人们在讲述和铭记敏感往事时所涉及的个人与集体记忆。
因此,《成为祖先的幽灵》是后纪实美学实践的典范,作品用诗意的艺术语言统领着碎片化的零散信息。它所带来的知识是开放的、含蓄的,更因艺术家关注个人情感与敏感情绪而显得不够完整。尽管如此,作品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含糊的法国殖民传统及其对塞内加尔社会的长期影响。具体而言,它指向了殖民引起的多层次移民流动,以及对民族身份认同的重新洗牌。
阮俊于1976年出生于胡志明市,随后在美国长大,目前生活和工作于越南。他在2006年成立了艺术团体“螺旋桨小组(The Propeller Group)”,该团体通过批判性视角进行媒体和广告创作。2007年,阮俊又与他人共同创立了越南最有影响力的独立艺术空间“Sàn Art”(意为“艺术平台”)。他的多媒体艺术实践围绕着叙事和信仰建构展开,研究个人经历如何与历史交错碰撞。他的影片常常将虚构内容与档案影像相结合,以此反思盘根错节的虚构投射与历史记忆。
创作语境和艺术驱动力
寻常而含糊的殖民历史

《登巴和杜邦》。 塞内加尔和法国士兵的纪念碑于2004年迁至达喀尔并改名为“步兵广场”(Place du Tirailleur)。
(网络图片)
“塞内加尔步兵团”(tirailleurs Sénégalais)是拿破仑三世下令于1857年成立的法国殖民军团。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步兵团不止有塞内加尔士兵,还包括法属非洲各国的士兵。到了1960年,大多数法属西非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自19世纪以来一直被法国殖民的塞内加尔也不例外,于是步兵团宣告解散。这些非洲士兵不仅参加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还在二战后帮助法国在各地——特别是印度支那——备受争议地镇压反殖民运动。由于胡志明与法国当局谈判失败,印度支那战争于1946年打响,直到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Diên Biên Phu)战役失败而告终。法军溃败后不久,部分非洲士兵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镇压另一场重要的法国殖民地冲突,被迫在非洲领土上与文化亲缘更近的敌人作战。
“第一批非洲士兵于1947年抵达越南北部的河内市和海防市。自1914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一直是法国的储备军集中地。截至停战之时,该地区为法国提供了60,340名参战士兵。其中近3000名非洲士兵阵亡,3706人受伤,还有2546人因病而被遣送回国。”历史学教授露丝·吉尼奥(Ruth Ginio)教授强调这些士兵往往没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就匆忙上阵。为了提振士气,法国军方大规模授勋雇佣兵,其数量之大,几近荒谬。阮俊的影片中也有步兵着盛装参加授勋仪式的档案录像。许多塞内加尔士兵都受到了精神创伤,不过他们都是自愿参军并奔赴印度支那前线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有机会前往麦加朝圣、赢得更多收入或者提高社会地位。
作品《成为祖先的幽灵》将焦点放在战后带着越南妻子和(或)儿女回到塞内加尔生活的士兵的后代身上。作品并未直陈这些士兵在战争中的责任,也未质询他们试图打击反殖民力量这一事实。吉尼奥回忆道,这些士兵的确是为捍卫“压迫自己的殖民统治”而战。在影片中,他们是听命于法国殖民政府的士兵,但在若干的对话中浮现着隐晦的暧昧感,勾勒出他们与法国之间复杂而含混不清的关联。发生在西贡的一幕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时法国刚刚战败,一名士兵对他的越南籍妻子说:“我们输了这场战争”,顿时让人觉得这里的“我们”具有讽刺的意味。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关系愈加复杂,更让人无法清晰界定个人的身份认同。三种身份的人在这里交织混杂:法国人、越南人(与法国人并肩对抗北越的南部地区)和塞内加尔人。而作为不具有法国国籍的人,后两者更值得关注。就像影片中一位塞内加尔士兵说的,当法国需要他们参战时,他们就是法国人。不过,视频中所有的受访者都说法语,反映了法国殖民传统的深厚根基。
混杂身份与湮没无闻
对当地的越南女性而言,这些塞内加尔士兵能给她们带来财富和庇护,尽管她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文化习俗和样貌有些恐惧,但还是渴望与一些士兵确立关系。对当地女性而言,这些士兵可以“满足她们的需求,不用再卖身求活。”有些士兵在当地结婚生子,并在战后把妻儿都带到塞内加尔生活;也有些把妻子留在越南,只带着子女回国,甚至有些带回去的都不是亲生子女。吉尼奥指出,有些越南女性把自己生下来的混血儿(métis)明码标价地卖给了来自非洲的生父。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全家福档案照)
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教授安·斯托勒(Ann Stoler)注意到法国人对混血后代的担忧,并指出这些“混血儿群体”被视为殖民秩序的威胁。她还从更广泛的层面强调了异族通婚对任何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上带来的巨大威胁,因为混血儿群体跨越了地域、习俗、规范和疆界等诸多领域。越南女性和混血子女的到来遭到了塞内加尔当地社会的排斥。阮俊采访了达喀尔越南社区的居民,发现当年很多家庭都以这些移民为耻。有些越南女性被迫藏匿起来,或者被当地人视为异类,或者只能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得到认可。可是大多数越南女性只有追随丈夫这一条路,因为如果留在越南的话就会以叛徒身份被处死。即便她们心心念念想回到越南,但也从未回去,而且一般从不谈论自己的祖国。据阮俊采访的塞内加尔士兵后代博巴‧迪亚洛(Bouba Diallo)所言:“一旦她们离开越南,就被彻底遗忘,一切曾经在此生存的印迹全被抹去。”其中一些越南女性已经离世,而她们的孩子无从知晓母亲的身份和历史。留给后代的只有寥寥几封书信或几张黑白旧照,于是他们开始质疑这段被湮没的历史。这些女性实际上是家庭的顶梁柱,她们的后代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继承母亲所开创的家业。从中,阮俊意识到信息传递的重要性:人们要记住什么?又要忘却什么?
玛丽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首创了“后记忆(postmemory)”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在上辈记忆影响下成长的儿童——对她个人而言,就是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该概念也适用于这些塞内加尔士兵的后代,因为他们只能从几乎一无所知的过去中寻找身份认同。有些退伍回国的士兵从不让子女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流淌着越南血脉的混血儿在成长过程中发觉自己和别人不同,但又不明就里。接受阮俊采访的马卡杜‧恩迪亚耶(Macodou Ndiaye)也承认,19岁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混血儿。他有两份不一样的出生证,而且父亲一直以来都否认他有越南血统。不同的个人历史使得这些塞内加尔士兵后代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同的认知。例如,阿布巴卡‧士(Aboubacar Sy)又名华人布巴(Bouba Chinois),他拒不接受塞内加尔国籍,因为自己的塞内加尔父亲抛弃了越南裔母亲和八个子女;在另一个案例中,莉莉·巴约米(Lily Bayoumy)直到1988年“父母”去世时才发现自己是在奠边府战场捡到的养女,而她的非洲教育经历也促使她更加认同自己的非洲血脉。片中一位角色自豪地高唱南越(越南共和国)国歌“呼唤公民”(旧名“青年进行曲”),呼吁人们“打倒侵略者,解放越南……”。1975年越共占领南越,攻陷西贡,这首歌也在越南销声匿迹,不过还在越南侨民中流传。达喀尔当地的越南人听到这首歌,也许会觉得意外。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歌唱越南国歌)
目前大约有3,000名越南裔居民生活在塞内加尔。他们实际上有自己的组织,部分成员于2016年成立了“金会”(Kim Hoi)——塞内加尔的印度支那越南人协会。虽然塞内加尔士兵后代的故事不是什么禁忌,但终归属于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有些越南文化特征实际上已经渗入达喀尔的当地文化,比如越南特色菜肴(特制炸春卷)和武术,但当地人民无法与越南社区的历史产生共鸣。在学术领域,露丝·吉尼奥提到:“公共追思活动和学术研究重点关注这些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而非参与法国备受争议的镇压反殖民战争。”斯托勒认为,法国尚未承认自己的“种族化历史”,时至今日,法国殖民历史的阴魂犹在。阮俊作品的标题明确指向这些活跃的殖民主义幽灵以及历史遗留的越南文化。阮俊曾研究过越南船民问题,在他看来,质疑史料编纂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历史被感知、传递和记忆的方式同样亟待质询。在达喀尔的所见所闻令他着迷,所以他希望反思记忆的过程、复杂性、影响和缺失。“我将个人实践投入于探索叙事的局限性,包括叙事的力量以及叙事如何被滥用。”
艺术家的研究维度
开放式研究手段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全家福档案照)
阮俊之所以喜欢从事研究,是因为研究并非只带来预料之中的结果,而可能进入截然不同的探索路线。刚开始的时候,艺术家的研究重心并不在于达喀尔的混血群体,而最终呈现的作品恰如其分地验证了“误入歧途”所能带来的艺术硕果。
阮俊最初是想要研究不同被殖民者是如何凝聚起来、团结实现南南合作的。他特意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去寻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将塞内加尔士兵与印度支那士兵联系起来的事件。在研究助理简·普约尔(Jane Pujol)的帮助下,他搜索了法国军事档案,却找不到所需的证据。各地的士兵往往分开管理, 各自组成不同的团体,相互之间没有交集。他在达喀尔参观了开放于1997年、专门记录和保存退伍士兵证言的军事博物馆,还采访了参战的老兵。但他找不到一丝有关“团结合作”的证据,这些士兵反而把为法国而战看作光荣。所以阮俊自己都说这是个“失败的”研究项目,但他的实地研究意想不到地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他在接触到了达喀尔当地的越南社区,被当地居民的经历深深吸引。在了解到有些生活在非洲的越南人并不了解塞内加尔士兵后代的故事后,他调转了研究方向,致力于研究他们的口述证言。
在历时八天的首次达喀尔之行中,阮俊结识并采访了当地居民,第二次前往时用了三周的时间拍摄影片。他承认实地研究太过仓促,时间长一些就更好了,不过他还是设法与当地社区建立起一种信任和长期的关系。为了与士兵后代碰面,他与原材料公司(Raw Material Company)进行了合作,由喀麦隆裔策展人柯尤·扣沃(Koyo Kouoh,也译作光洋)出资成立了一个类似于“Sàn Art”的艺术空间。合作方的团队将他介绍给了居住在艺术空间附近的越南社群。阮俊为受访者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他让受访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生平,并且录下了采访过程。就这样,他以数十小时的记录资料作为项目基础,但却没有直接使用这些素材。最重要的是, “受访者自述”这一行动能够让他更好地了解这些人的生活背景和关注点,同时给予他们表达自我的机会。因为这个圈子里都是越南裔居民,所以他认识的人越多,就能接触到越多的越南裔家庭。

分享记忆:艺术家实地研究的纪实摄影
在开展实地研究之余,阮俊还继续搜寻有关塞内加尔士兵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档案材料。他特意从网上找了些影像片段,并从法国陆军通讯视听办公室(Établissement de communication et de production audiovisuelle de la Défense,简称ECPAD)和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 d’Outre-Mer,简称Anom)收集了照片——前者负责记录法军参加的所有战役的影像,而后者位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是最重要的法国殖民地档案馆。这些档案资料佐证了艺术家在实地研究过程中收集的叙事,让它们找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应有的位置。历史学家往往将历史档案与口述证言相关联,而阮俊另辟蹊径,并没有在它们之间创建任何直接联系,而只是将这些不同的叙事模式和对待历史的不同方式并列在一起。从官方影像到家庭合影、亲人口述的往事或深藏内心的记忆,艺术家巧妙地运用了各种记录和传播历史的载体,从不质疑内容的合理性或一致性。
合作式研究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权利和义务向本族人民展现自身的内涵,因其责任重大,既不能交由外人,也不能任由外人篡夺。”毛利电影制片人巴里·巴克莱(Barry Barclay)的话表明,让公众了解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社区绝非易事。越南电影制片人和理论家郑明河(Trinh T. Minh-Ha)也曾于1982年赴塞内加尔拍摄了纪录片《重聚》(Reassemblage),这部享有盛誉的作品以村民为主人公,质疑了由外来者去呈现本地文化的实践。郑明河建议在这样的社区“近旁说话”,该做法是“避免了对说话者人格物化,并非指向性的方式(仿佛远离说话主体或主体不在场),而是一种反思式的讲述,可以非常接近主体,但是无需控制或索取。”
阮俊并未妄图描述这个特定社区的文化和习俗,而只是强调沿袭沉重的历史时所面对的复杂情境和种种困难。他的艺术实践突出了记忆的过程——牢记和忘却——而不是系统性地观察这些塞内加尔士兵后代在达喀尔的生活。不过,他的电影赋予了该群体表达自我的机会,通过收集第一手口述证言来反映特定社区的独特性,这类似于民族志学者常用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尽管他短暂的逗留不足以让他深入接触该社区。为了避免索取、挪用或物化这些塞内加尔籍越南人的故事,同时又要与他们保持足够的联系,阮俊选择与部分社区成员深度合作,经由他们来呈现自己的历史。除此之外,他还建议部分居民把个人经历写成虚构剧本并表演出来。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父与子,四联屏)
阮俊常用虚构内容来填补历史空白、弥补档案缺失,这点在他研究船民问题时尤为突出。在他采访过的几位达喀尔女性中,有一位叫安妮-玛丽·尼安(Anne-Marie Niane)的受访者以自己的越南母亲为题材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她母亲来到塞内加尔后如何面对当地一夫多妻制等文化差异的经历,正是这个发现让阮俊萌生了将虚构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想法。阮俊以这部小说为原点,除了建议她进一步丰满虚构叙事,还邀请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创作。艺术家没有引导成员间的讨论或对话题的态度:在个人经历的启发下,尼安虚构了一个西贡旧时的场景,讲述了一名塞内加尔士兵行将离越之际与越南妻子之间的故事;马卡杜‧恩迪亚耶(Macodou Ndiaye)描绘了一对达喀尔父子的争执——儿子责备父亲隐瞒了自己的越南血统。最后一个场景来自梅莉‧蓓耶‧迪乌夫(Merry Bèye Diouf),她虚构了一位塞内加尔年轻女性与越南裔祖母之间的对话。经过众人多次碰面和讨论后,不同的场景得以体现整个社区的参与和投入。对安妮·玛丽尼安来说,写剧本是重建历史的一种方式。“当记忆褪去时,想像力可以填补空白。”在接受艺术家私下采访时,她强调了该做法的积极影响:“通过重写故事,我们可以重塑生活。”除了这三个虚构故事场景,《成为祖先的幽灵》还呈现了访谈和档案资料中的部分内容。所有场景在影片中轮番上演,参演者要么是在演绎他人,要是在本色出演时也至少知道镜头的存在。艺术本人家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影片中,在采访中也从未露面。
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
多元声音和混杂属性
“成为祖先的幽灵”包括数个长短不一、没有因果关系的并置篇章。尽管阮俊通过编排展现出一个有头有尾的叙事,但其中并无线性叙事结构。在沙迦双年展中,环绕四周的四面屏幕朝内而向,坐在“屏幕圈”中的观众可以欣赏不同屏幕上同时播放的影片。四幅图像相互补充,彼此间开展对话,透过多样的表达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多重视角。
影片始于一个非虚构场景,拍摄了一位身居客厅的不知名达喀尔男性。他的故事源自怀了他的越南裔母亲在1956年给父亲写的信。他的父亲那时已经离开印度支那,而母亲留在西贡。读信的时候,其他屏幕上会弹出档案影像,包括这封信的特写镜头,还有一身戎装的非洲士兵父亲和身穿越南传统服饰的母亲的合影。阮俊将这封信视为关联观众的起点,以此构建语境并吸引观众。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西贡剧本,四联屏)
随着第一幕的戛然而止,轻柔却稍显戏剧性的转场音乐将观众引入下一幕。一位手拿麦克风的女性正在朗读剧本里的对白和演出说明:“室内。公寓,西贡。夜晚。”与此同时,表演正在另一面屏幕中上演,出镜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越南女性”和“高大黝黑的男人”瓦利。两人正在争论是否要离开越南,可见当时的法国殖民统治即将落幕。一些档案照片(主要来自战争时期)时不时打断场景的连贯感,而且也出现在其他屏幕上。比如在一个镜头中,法国国旗被扯落,象征着法国战败。在这些记载往昔的黑白影像中,叙述者一动不动地站着,手里拿着一张年轻女性的肖像。
音乐响起,再次将观众引入下一幕。这一次,受访者在自家公寓里吟唱着南越国歌。歌声刚响起时候,一段纪录片也在同时播放,影片里的一群孩子正在观看军事庆典。仪式上,一位法国军官正在向非洲士兵颁发勋章。随后,影片又加入了两场虚构的舞台场景,包括一位外来叙述者,以及关于社区过去和现在状况的图像。这一幕以一段音乐收场,一位身着塞内加尔传统服饰的年轻人用沃洛夫语(Wolof,塞内加尔民族语言)唱道:“莫偷懒,勿放弃。别否认,不离弃。”其实,音乐在转场的时候就已经播放过了,只不过转场音乐没有歌词。最后一个场景类似于音乐剪辑,主要通过慢镜拍摄当地生活的日常片段,囊括了全体社区成员的肖像。最后停留在屏幕上的是一些全家福,其中有些人手持先祖的照片。歌手乌斯曼‧塞里涅‧穆巴克‧诺雷尼‧赛克(Ousmane Serigne Mbacke Noreyni Seck)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与之前哼唱越南国歌的将军形成了鲜明对比。艺术家为影片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视角,并通过全家福将作品的尺度从个人层面提升到集体层面。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操练武术)
秉承这样的理念,影片保持了开放的结构。如同具有混血身份一般,作品挣脱了单一线性语言的藩篱,游走在各种风格之间:多重声音和个人叙事混合并置,现实与虚构在其中无缝交叠。众多的口述证言以非层级结构组织划分。无声的黑白档案影像补充了叙事,但未加以解释。艺术家还加入了社区成员练习武术和太极拳的无声片段,这些都是由父辈传给后代的原生文化遗产。因此影片的表达方式也极其多元,涵盖了个人口述、歌曲、无声影像和书面剧本等诸多形式。音乐成为不同场景间唯一的联系纽带,诺雷尼的歌声将这些分散的个人与集体记忆、缺席与在场、梦境与现实串在一起,从而为超越历史传承、重新定义社区开辟了新的可能。
支离破碎的记忆流动
从结构上看,影片遵循着人的记忆逻辑,包括了断裂、矛盾、倒叙以及相互交叠并彼此呼应的不同时空坐标。共时性体现为艺术装置的四联屏,也蕴含在在艺术家剪辑影片时对时间和视角的叠加处理。电影摄影语言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只有一条人为设定、可以反复激活的时间线。以第一个虚构场景为例,叙述者是正在争论是否要离开越南的夫妇的女儿。鉴于剧情发生在过去,所以女儿实际上比彼时的母亲还年长。她代表父母再现了这场争辩,她一个人的声音与父母两人的口型差异营造出一种距离感,就像人们在做梦或回忆时的感受。不同的人在记忆中重组时间和往事的方式也不一样,特定的纪念物会突然现身或反复再现,带来意想不到的回忆。同样,影片中的一些画面或镜头反复再现,某些对白不断重复,如同循环播放一般。物体的特写镜头不仅反映了记忆对细节的依恋,还说明简单手势(如此处梳头的动作)或寻常物品可以触发多少记忆。回忆就像漂浮的纪念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而且大多数场景都以慢镜拍摄,这些虚构的片段以模糊的图像收尾。此外,游移的长镜头似乎也模仿了游荡的心灵。举个例子,手持全家福的人物在镜头中通常是纹丝不动的,而摄像机先是向他们靠近,然后再度拉回,暗示了要把过去留在身后。
最后一个虚构场景直接指向法国导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他因关注记忆问题并在影片中融入档案图像而广为人知。例如片中年轻女子与祖母的对话,借用了雷乃作品《广岛之恋)(Hiroshima My Love)中法国女子向日本恋人问起广岛时的措辞和旋律。男子说女友在广岛什么都看不到,但她说她看到了一切,哪怕广岛被轰炸时她不在现场。在《成为祖先的幽灵》中,一个年轻的塞内加尔女孩在为祖母梳发,问起了一无所知的过去和陌生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你记得什么?”“(…)我记得印度支那的一切。”“对于印度支那,你什么都记不得,什么都看不到。”叙述者将对答混在一起,让人搞不清说话的主体。这与记忆内容无关,而是关乎如何记忆以及由谁来记忆。“和你一样,我知道什么是遗忘。我有记忆力。和你一样,我也忘了。” 雷乃电影中的法国女子如是说道。此时此刻,遗忘和记忆密不可分。时间冲刷了一切,90岁高龄的越南裔祖母行将就木,但她的孙女坚称要留住记忆。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牢记历史,尤其是不属于我们的过去?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我记得)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人类正是因为不断牢记历史,才导致不堪历史的重负。相反,动物看起来更快乐,因为它们过着“非历史的”生活。尼采并非鼓励人类效仿动物,而是质疑人们过度渴求抓住历史、培养历史知识的做法。因此,他赞扬了遗忘的好处,因为遗忘有时是健康且必要之举。《广岛之恋》中的法国女子承认她终将忘记自己的恋人,“他终将成为一首歌”。也许塞内加尔士兵后代所背负的“后记忆”将化为一首歌,这也是影片结尾诺雷尼所唱之歌的内涵。
亲密与关爱
身为叙述者,女孩和祖母之间的对话充满爱意和理解。当女孩为祖母梳头时,另外几面屏幕上会显示出不同代际的女性相拥或紧抱彼此的图像。一举一动尽显轻柔,节奏与缓慢而用心的梳头动作相一致。影片从整体上看没有任何暴力元素和公开冲突的迹象,就算是父子间的争执也能以和气收场。阮俊镜头下的各色人物都背负着错综的人生经历和种种谎言,但他们似乎总有应对之道,而且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命运归咎于他人。大部分场景采用了和缓的拍摄手法,其中不乏慢镜拍摄,镜头也一直踩着轻柔的步点。在第一个场景中,当马卡杜读信时,镜头仿佛要将他包裹起来,来安慰他。他极为缓慢地读着越南母亲写给他的珍贵家书,没写清楚的地方要停下来斟酌,纠正母亲的法语表达。在这感人的场景中,艺术家把时间留给了观众,让他们体味这份感情。
因为大多数受访者都直视镜头,凝视着参与阮俊调研过程的观众。观众与艺术家一起欣赏受访者编写的演出场景,与之共享这些亲密时刻。在沙迦双年展上,视频装置被放在室外,地面铺满细沙,四面屏幕墙的由隆起的沙堆支撑。观众在装置中央或坐或站,四周被影像和声音所环绕。除了头顶的广阔天空和远方的城市,装置周围空无一物。这番布置营造出的沉浸式体验令人感同身受,恰如其分地映射出如梭的岁月。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双重肖像)
阮俊作品《船民》(2020)从不同的视角探索了人类记忆,在谈到这件作品时,他强调要用关爱来面对历史:“在后殖民语境下,我不认为历史是可修复的,因为过去有太多的东西遭到了破坏;但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还是非常有效的。这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做法,既不会成为过去的牺牲品,也不会屈服于未来。因此,我相信互相关爱是精神力量的源泉。”
作品从第一秒开始就展现了阮俊的情感态度:当影片标题出现在黑色背景上时,字母内的阴影逐渐增大,而戏剧性的音乐明确了作品的整体基调。整个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受访者的脸部被特写,目光凝视着观众,他们似乎在与观众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最珍视的照片。当影片中的人物直视镜头时,他们也在凝视自己的内心深处,袒露出亲密。他们手中的照片超越了自身的意义。玛丽安娜·赫希教授在谈到后记忆问题时解释说:“除了口头或书面叙述,那些在大规模破坏中幸存、比表现对象更为长寿的摄影图像,实际上如同已逝世界的幽灵。照片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是历史存在的证据,是镜头所指对象的直接证据。但因为照片很快就获得了象征意义,所以它们势必超越对象自身的意义。”不过,这些幽灵在影片中似乎是是良善的。阮俊的剪辑手法和影片风格强调了这些人在平静地接受这段历史后所萌生的自豪感。鉴于此,我们所见的幽灵与安·斯托勒所说的在当下阴魂不散的“殖民毒性”幽灵完全不同,也与T.J.德莫斯(T.J. Demos)在那些聚焦于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的影像作品时中看到的幽灵相距甚远。《成为祖先的幽灵》并不着眼于当今塞内加尔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法国殖民参与,而是关注个人在亲密关系中留下的伤痕。正如影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塞内加尔士兵的后代并未被边缘化,但影片也没有提及他们是否能融入现今的塞内加尔社会。就像片名里“成为”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影片面向的是开放的未来——承认历史,但不被历史羁绊。
结语

《成为祖先的幽灵》(2019)。视频截图(全家福,四联屏)
在创作《成为祖先的幽灵》的过程中,阮俊结合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用合作式、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去切入档案研究。他将自己收集的口述证言与虚构的个人故事交织在一起,并采用动态的对话式手段开展实地研究。时长28分钟的影片正是这些视听素材“拼贴”的产物,彰显了多元声音。它为这个身份和历史长期被忽视的社区创造了一个关键的空间,让人们对这个特殊的社区产生一种情感的、审美的、而理性的认识。尽管碎片化的叙述有时令人困惑,但记忆本身就是敏感且难以传达的主题,记忆所代表的负担借由一系列的形式、缄默、坦白、推测和追忆表现出来。观众由剧本引导,但仍可以自由发挥想象:作品几乎从未提及语境,也省略了针对特定案例和口述证言的真实要素。正因为如此,影片留下了大量空白,恰恰可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探求欲。特别是,作品没有暴露越南女性移民后的生活条件,也没有说到殖民战争后归国士兵与当地民众之间必然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些士兵后代的生活状态、社会地位、个人抱负以及他们从特殊身份中继承的遗产也不得而知,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们会练武术。再影片中,观众可以捕捉些许线索,但无法从整体上知晓他们的经历和身份。
因此,《成为祖先的幽灵》是后纪实美学实践的典范,作品用诗意的艺术语言统领着碎片化的零散信息。它所带来的知识是开放的、含蓄的,更因艺术家关注个人情感与敏感情绪而显得不够完整。尽管如此,作品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含糊的法国殖民传统及其对塞内加尔社会的长期影响。具体而言,它指向了殖民引起的多层次移民流动,以及对民族身份认同的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