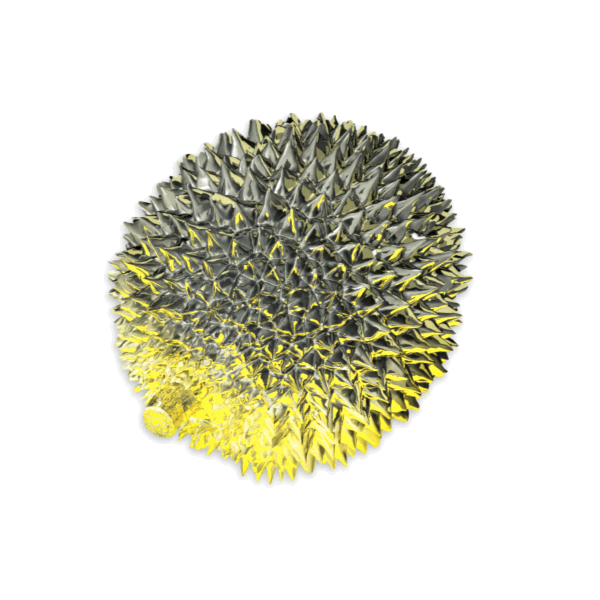研究综述
2018年秋天,我在诸多机缘下帮助一位德国朋友找到了失散半个世纪的亚洲亲人,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横跨德国、瑞士、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潮汕地区的家族团圆。寻亲之旅的唯一线索,是一张背后写有模糊地址的建筑照片。这栋位于今天的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西陇村的两层建筑建成于上世纪20年代,它沿袭了潮汕传统建筑样式“下山虎”(又称“爬狮”)的空间布局,却弃用了同时代主流的砖木结构和版筑外墙。盛行于明清本地建筑中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和嵌瓷工艺均未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由产自不列颠的混凝土勾勒出的优雅线条和源于苏格兰的铁艺纹样。除此之外,建筑外表被饰以廊柱、拱券、百叶窗、壁画和清丽彩漆。此去经年,我与居住者来往频密,协助他们增补了族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德两家联系的中间人。
从这座家宅开始,我——这个充满疑惑的当代闲逛者——在岭东沿海地带走访了数十个类似西陇村那样有海外交流史的村庄,定位了大约60座建造于1870-1949年之间“混合乡村建筑”(潮汕人称之为“洋楼”或“番仔楼”)。它们中的大多数,几近荒芜。关于这些民居的史料寥若晨星,但一些晚近的研究表明(如Knapp, 2010),远在“洋楼”于潮汕落地之前,各种形态的“混合乡村建筑”从18世纪便开始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中出现。这种说法逐渐在田野考察中得到印证。走访中,我多次从耄耋老人的口中获知,他们在潮汕所居住的大房子往往拥有一个遗留于在南中国海彼岸的孪生兄弟。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对一座房子念念不忘?
使得这项研究持续到此刻的动因远非是它们看似与今天落后的乡村格格不入、也无从符合任何风格的建筑形式,而是关于这些人造物如何通过一种跨越国家边界的“区域分析”(Skinner, 1977),具体地体现和突破某种“或地方或全球”的叙事,以呈现出一种持续发生转变的“地方眼光”(Wang, 1994)。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解这些建筑的“表皮” (Semper, 1989)及其存在语境,去阐释后代居民当前所面临的一些普遍疑惑甚至痛苦:一种在(后)工业时代中难以为继的关系曾经如何在这些场所中得到体现和塑造?我们又应该如何以后现代的身体去体悟这些沉积了整个地区现代历史、展现了20世纪(及其前后时代)的数次思想革命、以及印证了居民生产生活方式持续转变的人造景观。简而言之,我所在乎的是这些跨越海洋分布的房屋的物质性及其纷繁的呈现和使用方式,也包括了其自身各部分、田地、社区、和景观的语境(Glassie,1975)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性作用。
这项研究仍然处于“家屋社会” (Lévi-Strauss, 1983) 的框架之中。在过去百多年里,这些房屋作为关系的容器巩固了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家庭,由此基于并超越家庭关系的分析几乎是这项研究的底色,婚姻、家庭和宗族必然是研究的基本切入点。但兴许更有趣的是,通过分析这些住宅、村舍、市镇和区域的构造和功能,以及次场所当中诸如界限、开口和装饰和日常用品,我们可以从某种关于记忆与修辞的视角去洞悉更隐秘的关于观念、思想和宇宙观问题,和更本质的关于如何建构关系以及如何“栖居”(Heidegger, 1993)的问题。今天幸存下来的房子有一大部分建造于1929到1939年间,兴许是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启了这波建造浪潮,而二战的在亚洲的全面爆发为其画上了厚重的逗号。研究将从这个阶段开始逐渐向前向后蔓延。历时性维度的加入既是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使然,既通过长时段的观察建立某种地方、区域和全球规模上的普遍性,以此更好地验证这些对象产生的具体条件和当下的新的普遍性;同时也是对时下的乡土研究、民族国家话语和过度多样性的规避。正如过去七年我在当地所从事的电影节策划那样,它既不迎合身份认同也不满足民族自豪感,但它终究能够回到脚下去解决一些问题。
我在这里出生和成长。作为研究者,我幸运地通晓这个区域的几种语言和口音,但更重要的是,我也会在这里死去。所以我应该无法成为一个保持充分距离的客观观察者,因为我需要对它的过去的阐述和未来的选择负责。如果这项研究最终能够产生什么成果,我想它们必然是诱导性的。我期望未来几年的工作能够以更加体验性的方式卷入受众,诸如建立起一个简单的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档案供后来的研究者和漫步者使用,也能够继续利用视觉语言和展陈力量引发公众的兴趣和讨论,我甚至渴望以此去打动或干扰一些决策者。在东南亚,有一定数量的“混合乡村建筑”已经得到保护和修缮,并在旅游经济和基金会制度的关照下得以暂时安宁或持续调用;而在海的这边,在我有限在场的几个月中,这些幸运地没有被城市化进程取缔的“危楼”,也正在“文件”的摧枯拉朽中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被破坏性修缮或夷为平地。很快,老人们也会携带着残存的记忆和关系离开。前面所提的那座房子,居住者和所有者也因为拆迁问题展开了家庭内部的拉锯。这项研究也注定需要面对新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选择,因此这些细节、建筑和空间以及围绕着它们的情感、叙事和想象也需要新的注解和对待。
研究对象及范畴
在这项研究中,建筑将作为一种具体的现象受到讨论。它们没有区别于其他建筑样式的“种类”,只有不同的使用情景,从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以满足人在实质上和精神上的所需。所以有异于以往的建筑史学研究,我将不会为“潮汕洋楼”下一些明确的时空定义。“不会”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无能为力。例如在时间跨度的向度上,哪怕我们能够确信这样的建筑曾在20世纪20-30年代有过一个建造的高峰期,我们也很难忽略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到建国前夕、甚至是1966年侨联全面停止工作之前的那些特殊案例。我们也无法忽视改革开放之后在村庄的“新乡”地带普遍存在的“混合安置房”,更无从对这些建筑在土改、文革和乡村工业化中所残留的显著痕迹视而不见。更何况,当中的一部分直到当下仍在受到使用、改造和重建。诚然,这些建筑的兴衰起落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但事件史的方法与当地居民切身感受到的历史有显著不同。
为“潮汕”下一个严谨的地理定义也不现实。今天由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座城市构成的“潮汕地区”,在过去短短的百年中并非一成不变。与“潮汕”接壤的梅州市大埔县、丰顺县和福建诏安县仍然居住着不少使用潮汕话的居民。同时,东南亚国家中亦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潮汕人社群。在这项研究中,“潮汕”更倾向于被视为一个心理边界或宽泛的身份认同,这将有利于避开部分“潮学” 研究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也为研究提供更具关联性的基因。这项研究也有意将这一历史阶段的地理中心地带从拥有殖民史背景的汕头港转向樟林港,后者曾于清嘉庆年间和清道光年间经历了短暂的盛衰。樟林既在时空上具有先发性,其居民开始以现代方式从事海外交往的历史远早于“冲击说”(Fairbank & Teng, 1954)的1840年和《天津条约》的1860年;樟林又在当中承受着明显的时空不对等——它既是现代性的前沿地带,却又恰巧因为潮州定埠汕头而错过了切身的殖民过程和线性时间的直接降临。围绕樟林的民居研究既是初步考察所显现的现象使然——这些建筑围绕着樟林港而非汕头港分布——也是对当前以殖民史为起点的现代史研究的某种回应。
“洋楼”概念则相对容易辨认些。这个名词目前所见最早的史料是《重建兴泉永道署碑记》(1864),但这块碑中所载的“洋楼”特指的是清道光25年英国人在厦门所建的领事馆,并非当前普遍所指的民居。今天,无论是在潮汕还是闽南的泉州和厦门地区,“洋楼”通常都取“外国形式的民居建筑”这一层含义,指涉那些以当地传统形式为主,与外来风格相结合或并置的民间建筑。除了洋楼之外,在前期的考察中,也有“番仔楼”(主要流行于民国时期)、“钟楼”(有些洋楼会在外墙挂一个时钟)、“侨厝”(指房主人的华侨或归侨背景)等叫法,最终选用1960年代以来更为通用的“洋楼”既更符合当下的普遍理解,也为南洋的考察工作留下空间。毕竟“番”字中本就有“南洋”之意,则称南洋地区的同类建筑为“番仔楼”显然不合适。通过发掘和追随人群的去向和归处,研究将持续在一种流动的眼光中获得观照。从樟林出发,研究会通过具体的个体叙事去寻找彼岸的房子进行比对。对于一个标准的有海外经历的潮汕人或家庭来说,他们往往会拥有一个“番外家”、“故土家”,还有一处“最终的家”(坟墓),如陈慈黉在曼谷和澄海隆都的家宅,邱氏在印度尼西亚和梅县的大屋,陈旭年在潮州彩塘的从熙供词和新加坡故居等。在潮汕的探访中,一些东南亚地方经常被提及,除了今天已经发展为都市的曼谷、雅加达、槟城和吉隆坡之外,马来西亚的吉胆岛、菲律宾的吕宋岛、印尼的泗水和邦加也偶有耳闻。这注定了这项研究也必须在流动中才能得以成型。民居形式演变是一种原型加调整的过程,文化因素决定了原型,气候、材料及技术是修正因子。(Rapoport,1969)这些房屋内部产生了怎样的关系,不同地方和指向不同时间的房屋又产生了哪些关联?文化如何形成了人们的选择,以影响这些房屋的建造、使用和观看,并再次塑造了关系和文化?流动作为潮汕文化的根源之一,将始终是这项研究的底色。
核心逻辑
在对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相关的历史情境进行说明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人与建筑的具体关系当中,以求梳理出一条研究的细分脉络。在一次建造行为当中,人意欲为何?建筑又意欲为何呢?本质上,人修建建筑,是为了赋予自己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建筑,与其他的艺术门类一样,是生活情景的具现,人的基本需求在于体验其生活情景是富有意义的。具现包括了“集结”和“物”,所以,建筑不止是一处庇护所,而是作为一种“物”本身和“存在空间”,既集中体现了人与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为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又通过建筑所塑造的空间和特性,让人获得方向感和认同感,从而让人感受到存在。这样的物和空间的持续存在和作用,兴许很大程度上是今天所谓“潮汕人”身份的物质基础。
但显然建筑不仅只有一种样式或用途。当我们去仔细界分这些房屋时,会发现有一些现象能够为另一些现象创造环境,允许一些特定的行为和事件的发生。这种现象就是场所,它们是由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而空间,就是一种场所系统,一些具体的场所和情境形成了空间的根源。此时,由于场所系统天然的差异,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边界开始显现。空间很大程度上由边界及其开口所定义,边界不是某种东西的停止,而是某种东西在此开始出现。边界存在的意义,往往也在于允许不同事物在此穿行。辨析空间的分野是这项研究的起手式,它们由宏大到细微,呈现研究的诸多层次。
首先是天地的分野。海德格尔在定义“定居”时,宣称世界介乎于天地之间,世界是凡人居住的房子。由此,世界是一种“之间”,人所居住的世界就变成了“内部”,从而也界定了“外部”。我们可以将内外部的分野粗略地划分为“自然场所”和“人为场所”,它们拥有简单的结构相似性。例如世界的上方边界是天,而建筑的上方边界是楼板和天花。在这些潮汕房子的天花上,我们发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蓝”,它们又被广泛地应用到墙体和门窗的涂装上。因为类似的蓝色大量出现在东南亚的“中国房子”上,有人又称之为“南洋蓝”。但实际上,至少在本地的一些明代建筑遗迹中,这种将天花刷蓝的做法已经颇为常见。我更倾向于将这种行为理解为“自然场所”与“人为场所”之间的对应,是居住者对于苍穹的尊崇和仰望。而天井的出现又是对于天地联动关系的保留。这个巨大的上方开口,在很大程度上模糊着空间的内外关系。房屋固着在大地之上,负阴而抱阳,风、雨、光的交替灌入,让建筑与屋外的山环水抱再次形成同构。在“洋楼”出现的几十年后,一些去除了蓝色天花和天井的新式建筑开始在规划有序的村庄中耸立,在遭遇现代性数百年之后,天地终究退场,关系开始崩坏。
造成场所发生差异的“特性”往往就发生在这样的分野当中。所谓特性,是场所中最为丰富的特质。它们表现为具体的造型和空间界定元素。当我们研究建筑时,我们会惯性地去对建筑的特性加以考证,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特性是表现是世界的最基本模式。因为特性往往取决于“物”如何形成。哪怕是未经系统训练的建造者,也必须依附于一套象征的造型语言。这种语言是由系统化的造型明确性所决定的。所谓明确性,是指使一个特殊的特性能够很精确地表达出来。人在存在空间当中持续吸收环境,又重新使建筑物在环境中形成焦点。因此带有特性的物不可避免地诠释了自然,并使其特性明显化,这让物本身变得很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象征化了自己对自然的理解。象征意味着将意义在目前的情境中解放出来,意义由此可以被转移。分野和特性的塑造共同创造了一个适合居住者自身的宇宙意象,一座房屋成为一个小宇宙,一个场所成为一个“中心”。
在这样的意义的生成和转移的过程中,蕴含着不间断地人对于自然的吸收和理解。人是如何理解自然的?自然的意义又在居住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尝试从天地、山、树、水来理解一座建筑的自然观。阴阳合和而万物生,一切均由天地两种元素结合而成。人们向天投射了超物质和超秩序的向往,而又向大地索取保护和亲近。山是二者的自然结合,它既有鲜明的外部性,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传统中被视为某种“去处”,也因其坚硬和耐久被赋予永恒的属性,却也被居住者视为某种包裹和生命来源。高高低低覆盖在山体表面的植物,是宇宙再生的印证,也是使得宇宙能够再生的方式。从山间或奔涌或慢淌而来的水,赋予了大地和植被以自我意识。耕地由水而发展,生活也由水而生动。作为“风水”的核心构成之一,水(包括泉眼、溪流、江河、海洋、蒸汽和雨)将会在这项研究当中被着重讨论。一个有石头、树和水的地景,就是一个世界。方向感和认同感由此确立,一种空间结构和场所系统也由此塑造。
而光与以上三者不同,光线是不稳定的。光拥有的是一种短暂的韵律,而短暂的韵律并不会改变构成场所的基本元素,但会对场所的特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光改变了一切的质感和颜色,改变了观看天地万物的视角和时长,由此,光塑造了“地方性”。在潮汕这样的海岸地带,光随着剧烈变化的气候和霎时间的风起云涌持续地产生着变化。变化往往是富有戏剧性的,而在伴随着光线的变化而明暗交织的建筑是充满诗意的。在潮汕的语境中,人们往往也强调阴翳。哪怕是在朝暮时分,斜穿过天井的光束也无法抵达房屋中心的厅堂。在阴翳里,祖先的阴魂享受着房屋的庇护,穿过伙巷的南风略过屋外的水池,卷着热浪从天井迅速逃窜。
我们会发现,在物、秩序、特性和光线面前,时间是一个恒常与变迁的向度。它使得空间与特性成为生活事实的一部分,将生活事实塑造成一个特殊场所,并在日积月累间形成一种场所精神。时间不是一种现象,而是现象的连续和变化所形成的秩序。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人们就可以通过调动这种秩序,例如将某种短暂性以具体化,又例如构建一种空间之间的路径,从而去“构筑”自己的时间。但场所是会变迁的,具体到这些潮汕房子上,场所是会流动的,它们跟随着先祖漂洋过海,在时过境迁当中完善自身,又在风平浪静时以崭新的面貌回归故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它所拥有的精神就一定会改变或消失。场所之所以为场所,是因为它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保存其认同,能够吸收不同的内容,适应各种用途,从各个维度被加以诠释。曾经盘踞在潮汕居民头顶的循环时间,兴许便是在这样的恒常和持续的变迁中得到维护。同理,当我们讨论保护和保存场所精神时,也往往意味着创造新的历史脉络。一个场所的历史,是其持续自我实现的过程。
至此,这项研究的核心逻辑开始显现。其中最重要的脉络,无外乎是对于自然场所的理解以及由此向人为场所的转换。在文化地景中,自然力量是在地生活的事实,人秩序井然又难以预计地参与其间。是人“构筑”了大地,同时人也表现了大地潜在的结构,让世界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我们所讨论的潮汕地区,拥有一个传统农耕文明的基底。在大地所主宰的地景中,人们往往以原型的“物”作为凝视对象;而我们讨论的潮汕时间,又恰恰因海洋而破局。在航海中,天总是比海更要紧。在天空所主宰的地景中 ,宇宙的秩序所具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房屋也主要分布于港口和河流沿岸中,如果按照城乡建筑特性来界分,这些位于乡村当中的房子理所应当地与自然环境关系紧密,但同时,港口所带来的集结又将其他地方的特性加以整合。这一切都让这些建筑拥有了更复杂的中间态。